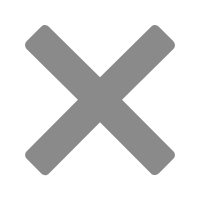-
老婆的白月光害死了我女儿
1
老婆带着我们的女儿和她的白月光一起应酬。
饭局过半,她让六岁的女儿一个人去给她的白月光买药。
女儿被前段时间震惊社会的虐杀犯残忍杀害。
等我赶到医院,女儿浑身是血,手里还拿着那盒过敏药。
“爸爸......原野叔叔的......”
随后,她再也没了气息。
那么小的孩子,身上的血还在流。
我崩溃的给老婆打电话,几十通后她才接起来。
不等我质问,老婆就在电话里吼道:“我让她买的药呢?拖了这么久怎么还没送回来?就知道在外面玩!”
不等我回答,电话就被粗暴挂断。
等我再打过去,显示已关机。
他们完全不顾我女儿的死活,他们是间接的杀人凶手。
既然这样,都来陪葬吧!
1
我的手上、身上,沾满了女儿的血。
她还那么小,那么小的孩子,怎么能流那么多血。
我看着女儿的尸体上盖上白布。
看着她被推进太平间。
整整一天,我都在处理女儿的后事。
医院的工作人员望向我的眼神中都满是同情。
四十八小时过去,我未曾收到来自妻子的只言片语。
十年婚姻,在这一刻,终究是走到了尽头。
我未进一粒米,未沾一滴水,眼泪已经流干了。
打印好了离婚协议书,静静地坐在沙发上。
终于,门开了,她舍得回来了。
然而,老婆进门的第一句话竟是:“我让你催女儿送的东西呢?送到哪儿去了?知不知道她害得原野受了多少罪?”
我满腔怒火堵在胸口,扯起嘴角冷笑。
送哪去了?送他妈太平间去了!
她不耐烦地脱下外套,随意扔在沙发上,一股陌生的男性香水味随之飘散,刺激着我的嗅觉。我眉头紧锁,习惯性地从抽屉里取出抗过敏药服下,这一幕恰好落入她的眼帘。
她嗤笑一声,语气尖锐:“你又在装什么?原野对酒精过敏,你哪来的过敏?既然这样,他住院了你怎么不去啊!”
“彤彤呢?让她滚出来给原野道歉!原野还帮她说话呢,他自己都被你女儿害得严重的住院了!看看你把孩子教成什么样子了?”
“我今天非得好好管教管教她不可!”
我将离婚协议书重重摔在她面前:“签字吧,别再为难我的女儿了,你没资格教育她,我给你们让路!”
她被我的话彻底激怒,一脚踩在协议书上,将其撕得粉碎。
“你女儿犯错,你跟我闹什么?原野大度不代表我能纵容她!”
“我管教自己的孩子,你就要离婚?你脑子有病?”
她的质问如同利刃,割得我心痛欲裂。
我猛地站起,眼前一阵眩晕,却仍坚持问道:“管教?请问我女儿做错了什么?她做了什么天理难容的事,需要你让她一个六岁的孩子一个人走夜路,给你的小情人买药?!你知不知道她被......”
“够了!”
我的话未说完,她已粗暴地打断:“没完没了了是吧?我让自己女儿送个东西怎么了?路上那么多人能出什么事?这点破事在你这哭爹喊娘,娇不矫情!她这么混账都是你惯得!”
说着,她从包里随手掏出一个小盒子狠狠地摔在我面前:“这个能堵住你的嘴了吧?赶紧让她出来,以后她的事你少插手!”
我看着她,突然意识到,女儿的事,告诉她又有何意义?
身为女儿的母亲,她根本不在乎啊。
她只关心她的小情人原野是否受了委屈,至于我的女儿,不过是个可以牺牲的棋子。
想到这里,我不禁冷笑,拿起那盒香水,轻轻一嗅,果然是她衣服上的男人味。
她连敷衍都懒得,给原野的礼物,随手也给了我一份,如同打发乞丐。
我深知自己对酒精过敏,从不触碰这些香水,因为香水里都放了酒精。
但原野明明标榜自己酒精过敏,却对它们爱不释手。
我这个老婆啊,从来就没想了解过我,更不相信我酒精过敏。
曾经,她送我的每一份礼物,我都视若珍宝,只因我爱她。
但这份爱,对她来说只是廉价,甚至不惜践踏我女儿的生命。
想到女儿,我眼眶又开始酸涩。
我平静道:“签字吧,我的彤彤以后不会再打扰你们,我的女儿不需要任何人的原谅,她本就没有错。”
唯一的错,或许就是生在了这个家。
听到这话,乔欣顿时面色阴沉。
“砰”的一声巨响,杯子在地上砰然碎裂,摔成无数尖锐碎片。
“礼物都给你了,你他妈还想怎样?女儿都这么大了你提离婚?我告诉你,离婚可以,女儿的抚养权你想都别想!”
“真是给脸不要脸!”门口传来关门的巨响,她愤然离去。
这是我十年来第一次对她如此冷漠。
她或许还以为我会像过去那样,吃醋、胡闹,然后等她回来,一切如常。
但这次,我要结束的是我们的婚姻。
我留下了自己签好的离婚协议,离开了这个生活了五年的家。
从此,我与她,再无瓜葛。
2
我暗恋了乔欣五年,与她携手步入婚姻又共度了五年时光。
然而,这段关系的起点与终点,都伴随着至亲的牺牲。
和她结婚,我妈妈付出了生命。
和她离婚,是因为我的女儿付出了生命。
一切始于我的母亲,她曾是顾家的保姆,用半生的时光细心照料着顾家的女主人,乔欣的母亲,乔太太。
母亲以她的勤劳与善良赢得了顾家上下的尊敬与喜爱,每年的薪资增长便是最好的证明。
那日,一场突如其来的火灾打破了平静。
母亲与乔太太外出归来,不慎遭遇火灾。
在生死关头,母亲没有丝毫犹豫,毅然决然地冲入火海,只为救出乔欣的母亲。
火势凶猛,母亲拼尽全力,最终救出了乔欣的母亲。
可是,她却葬身火海。
乔太太惊魂未定,望着母亲逐渐冷却的身躯,她泪如雨下。
在母亲生命的最后时刻,她向乔欣的母亲提出了一个请求——希望我能与乔欣结合,共度余生。
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请求,乔欣的母亲虽感意外,但念及母亲的英勇与牺牲,她含泪点头,承诺会促成这段姻缘。
母亲的离世让我痛不欲生,我的世界仿佛失去了色彩。
在众人的安慰与祝福中,我迎娶了乔欣,成为了乔家的女婿。
他们都说,我真幸运,虽然妈妈死了,但我却得到了一辈子的荣华富贵。
然而,我心中的痛苦谁又能懂。
如果可以,我宁愿一辈子孤独终老,哪怕是短命,只要妈妈活着。
乔欣在公众面前对我体贴入微,我们的婚姻看似美满。
但只有我知道,这背后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与辛酸。
乔欣的心中另有其人,是她的白月光原野。
她曾直言不讳地告诉我,这场婚姻只是她为了顺从母亲的意愿而演的一场戏。
戏内,我是她的丈夫;戏外,她的心却属于原野。
我试图用时间去感化她。
我以为随着我们女儿的降生,她能逐渐将心回归家庭。
然而,现实却给了我沉重的一击。
女儿的到来并未改变什么,乔欣的心依旧在原野身上徘徊。
而我,却在这场名存实亡的婚姻中越陷越深,无法自拔。
如今,回望过去,我意识到自己曾经的愚蠢与执着。
用母亲的牺牲换来的婚姻,最终却以女儿的离世作为终结。
这一切,如同一场荒诞的梦境。
3
这个困住了我五年的“家”,如今我终于能果断离开。
我带着彤彤的骨灰,回到了曾经与妈妈相依为命的老旧小屋。
未曾想,为彤彤挑选墓地竟然排了整整三天。
终于,到了那个沉重的日子。
我刚推开门,一股蛮力猛地袭来,将我踹倒在地,手中的骨灰盒险些脱手。
抬头一看,是乔欣。
她脸上的神情愤怒至极,而她的身旁,原野被一群保镖簇拥着,远远站着,脸上戴着医务防护口罩。
没等我站稳,乔欣早已跨过我的身体,浑身戾气的闯入屋内,大声呼喊着彤彤的名字。
她一间间房地踹开,却不见彤彤的身影,顿时怒火中烧。
她快步走到我面前,蹲下身,狠狠揪住我的衣领。
“彤彤呢?让她出来!”
我紧抱着骨灰盒,目光坚定:“我说了,你不配提彤彤的名字!现在,带着你的情夫离开这里!”
我的话彻底激怒了乔欣,她的眼神如同锋利的刀刃,直刺人心。
“管好你的嘴,否则我不介意让你学会怎么说话!”她威胁道。
“你颠倒黑白,污蔑彤彤做了恶毒的事,还想让我认错?乔欣,你是不是太过分了!”我怒不可遏。
正当我俩争执不下时,原野缓缓走近,摘下了口罩,露出一张布满红疹的脸庞。
他眼中含泪,委屈地看向乔欣:“没事的,可能孩子也不知道那是什么,害我过敏也不是她的本意……”
乔欣闻言,怒火更甚,转头对我吼道:“宋浩然,你看看你教出来的女儿!原野都这样了,你还想包庇她?”
我震惊地看着他们,心中涌起一股不祥的预感。
“乔欣,彤彤是你的亲生女儿啊!你在说什么胡话?你为了这个男人,连自己的女儿都不认了吗?”
乔欣仿佛没听见我的话,抬手就是一巴掌,重重地打在我的脸上,火辣辣的疼痛让我几乎失去理智。
“我警告过你,让你管好你的嘴!你教唆彤彤在原野的护肤品里加酒精,害他过敏,你怎么这么狠毒?还想让彤彤当你的替罪羊?”她怒不可遏地指责我。
我奋力反驳:“彤彤才五岁,她懂什么酒精?再说,那么刺鼻的味道,谁会闻不出来?乔欣,你为了袒护原野,连基本的逻辑都不要了吗?”
我声嘶力竭地喊着,试图将心中的委屈和愤怒都倾泻而出。
但乔欣的声音更大,她坚信是彤彤所为,甚至扬言要报警抓我。
“监控都拍得一清二楚,你还想狡辩?等我找到彤彤问清楚,就把你送进监狱!”
她恶狠狠地说着,仿佛我已经是十恶不赦的罪人。
“她人呢?让她滚出来!”
我望着她那双被愤怒蒙蔽的双眼,心中一片悲凉。
彤彤已经不在了,她却还要往她身上泼脏水。
4
我咬紧牙关,一字一顿地说:“你有什么证据证明!我绝不允许任何人诬蔑我的女儿!”
乔欣冷哼一声,迅速在手机上操作一番,然后将屏幕转向我。
画面上,一个穿着彤彤出事当天同样裙子的小女孩,步伐踉跄地走进卫生间。
她站在镜子前,从包里掏出一瓶液体,倒入洗手池上放着的护肤品中。
监控的时间戳赫然显示着两天前,而那时,彤彤正躺在太平间。
一时间,我笑出了声,一边笑着,泪水无声滑落。
原野这时插话,语气中满是虚伪的关切:“宋浩然,我只是想弄清楚孩子为何如此待我,并无他意。孩子嘛,现在教育还来得及,你不能纵容她做错事。”
我怒不可遏,猛地站起,抄起桌子上的咖啡就就泼在原野的脸上。。
“你给我闭嘴!彤彤的事轮不到你来插手!监控里的人都没确认就敢来诬陷,你就这么急着想当乔家的上门女婿吗?”
原野发出了痛呼,紧接着惨叫起来。
乔欣被我彻底激怒,积压已久的怒火瞬间爆发。
她一脚踹向我的腹部,我痛呼一声,手中的骨灰罐失控脱手。
罐子重重砸在水泥地上,盖子弹开,骨灰散落一地,显得格外刺眼。
那一刻,我仿佛失去了所有的痛觉,眼中只有那片刺目的灰白。
我嘶吼着,声音在楼道中回荡,却无暇顾及自己的伤痛,只能跪在地上,用身体护住那散落的骨灰。
乔欣居高临下,语气冰冷:“彤彤到底在哪?说!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”
我充耳不闻,整个人如同雕塑般僵硬。
她见状,怒火中烧,从保镖手中接过一瓶医用酒精,毫不留情地倒在地上,骨灰与酒精混合成一片污浊。
她弯腰抓起一把,狠狠地朝我脸上抹去。
冰冷的触感让我颤抖,而她的动作却愈发疯狂,将骨灰与酒精混合物不断涂抹在我的脸上。
“今天,我就让你尝尝这滋味!说话!你聋了吗?!”她恶狠狠地咆哮着。
酒精刺激着受伤的肌肤,痛得我五官扭曲,惨叫声在楼道内回荡。
乔欣不依不饶:“想离婚?我成全你!但彤彤,你休想再见一面!”
她说完,用保镖的衣角擦净双手,拨通了电话。
“报警,不惜一切代价找到彤彤!让律师立刻拟好离婚协议,彤彤的抚养权必须归我!”她冷冷地吩咐道。
电话那头的人显然被惊到了,片刻后才小心翼翼地回答:“乔总,彤彤……她已经死了。就在您和原先生应酬的那天晚上,被前段时间的那个虐杀狂盯到杀了……”
“因为一直联系不上您,宋先生就为彤彤安排了墓地,今天正是下葬的日子……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