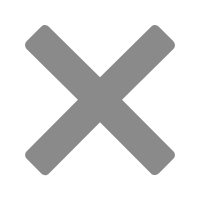-
嫁殇
1
为了确定婚事。
我第一次跟男朋友回山村偏远的老家。
可婚礼那天,新郎却换人了。
01.
“盖头遮住了脸,使她看不清前路;喉咙被灌满了糯米,嘴巴被针线缝死,使她口不能言;四肢被折断,钉在楠木上,使她动弹不得。”
我看着眼前的一幕,在最后一刻,我听到外头的锣鼓喧天响。
“吉时已到——”
哐当——
随着我一挥手,桌面上的玻璃杯被我打碎在地,我猛地睁开眼,被我枕着发麻的手臂逐渐恢复知觉,因供血不足而引起的冰冷也始终无法回暖。
“萱萱,你怎么了?”
房门被推开,我的男朋友李楠正一脸担忧的看着我,他蹙着眉头,看着被打碎一地的玻璃碎片,立马把我抱到了对面的沙发上,自己拿着扫把仔细清扫着。
他一边扫一边关切的问道:“你的脸色好差,是做噩梦了吗?工作也不用这么拼命啊,自己的身体才是最重要的。”
看着男朋友,不,准确来说是未婚夫对于我不爱惜身体而关怀的劝说,我感到无比暖心,冰冷的四肢也有了温度。
我点点头:“做了个梦......但是想不起来了。”
模糊记忆里只有一片片红白交织的虚影,再过一会,已经彻底想不起来了。
李楠打扫完之后走过来将我抱在怀里,手轻拍着我的脊背试图安抚我:“想不起来就别想啦,明天就要回家了,开心点。”
我依赖的蹭了蹭他的胸膛:“嗯,知道了。”
是啊,明天就要回老家了,回去结婚。
日子定在了正月十八,是李楠父母请人算的黄道吉日。
想到这里,我真的由衷感到幸福,遇到李楠真的是太好了。
我的老家在一个十分偏远的农村里,那里交通不便,信息闭塞,与之相对的,生在那长在那的人,多半思想也落后封建。
我的父母也不例外,自小被灌输太多女孩子要嫁出去,弟弟传宗接代等等的封建思想太多,而我却并不被同化。
我时常因为父母的不公而吵架,我的父母也并不会因此愧疚,反而因我的违抗了他们的命令,挑战了他们的权威而狠狠责打我。
在他们眼里我只是一个赔钱货,唯一的价值只是他们换取彩礼的工具。
在我初中毕业时,父母为了省钱给弟弟读书,让我辍学,并逼我嫁给同村的鳏夫换彩礼给弟弟赚生活费。
命运不公,我便自己争取,我偷了家里的钱逃了出去,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里打拼,并发誓再也不回去。
可只有初中学历的我,四处碰壁是家常便饭,我吃了许多亏,许多苦,累死累活赚取的工资还被父母威胁上交给他们做赡养费。
家里的弟弟一旦需要钱,父母就会打电话问我要钱,如果不给就威胁上我的单位闹,可我苦心多年好不容易爬上公司管理层的位置,我不想把事情闹太大,只能被迫每个月给他们寄生活费。
这件事一直持续到两年前,也就是刚和李楠在一起的那会。
他是公司新来的大堂保安,身量挺高,长得也颇为俊秀,可由于职位的差距,起初的我和他并没有什么交集,只是后来的机缘巧合下,得知我们来自同一个地方。
在一座陌生的城市,一个人流量那么大的地方,我们竟然还是同一个山沟沟里出来的,尽管我对那个地方没有丝毫留念,但我还是对他产生一丝亲切感。
后来我们逐渐熟稔,他对我产生了好感从而追求我,但那会我的事业心强烈,对感情的事并不热衷。
可在李楠的强烈追求下,我心里筑成的壁垒一点点塌陷,在一次契机中,我答应了他的追求。
02.
那时刚被同事穿小鞋,心情低落,正巧父母打电话来还弟弟欠的赌债,我心力交瘁。
李楠得知后夺过我的电话,呵斥父母这样的吸血行为,不因是我的父母而留有情面,反而因我的委屈,我的心酸而更加袒护我。
我看着他因心疼我而掉落的眼泪,我第一次对一个人产生了浓浓的依赖。
原来真的有人真心待我。
被他的情真意切打动的我理所应当的答应了他的追求。
奇怪的事,自那通电话起,我的父母再也没有打电话来骚扰我。
我的生活正式进入了正轨。
和李楠交往的期间,我享受了他无微不至的关怀,在这个快餐式恋爱的社会里,李楠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传统男人。
和他在一起两年,他却从未碰过我,理由是家风严谨,只有成婚之夜才能和妻子共度良宵。
我感受李楠对我的珍视,在不久前,我答应了他的求婚。
只是一想到......
李楠似乎察觉出了我的担忧,亲了亲我的额头,温柔的说道:“我知道你在顾虑什么,没关系,我们只是回去结个婚走个过场就回来了,有我在呢,别怕。”
由于原生家庭的缘故,我担心许多事,那因抵触而多年未曾踏足的故乡早已变得陌生,以及回想起父母的重难轻女,斥责打骂,邻居们的冷眼旁观,光是回想都让我喘不过气。
只会吸女儿血的父母,赌博欠债的弟弟,只有初中学历的我,没有任何家庭背景的我,却能够被李楠接纳。
说起来,李楠还是个体验生活的富二代,生活节俭,没有一点身为有钱人的架子。
虽然没有见过他的父母,但据他所说,父母也是白手起家,早年其实就搬离了农村,来到了县城做生意,抓住了商机的他们发了家。
李楠逢年过节也都是回县城,只是由于家里的习俗,需要回祖宅摆酒席。
我表示理解和尊重,农村总是重视很多风水和习俗,并对此深信不疑。
李楠的父母没有因为我的出身背景而嫌弃我,还早已提前替我们筹备好了婚礼,就等着我们回来结婚,受到重视的我更不能辜负这片心意。
说起来,具体的婚礼仪式我还不清楚。
只知道是一个中式婚礼,家里的老人很注重这种八抬大轿的仪式,繁琐的讲究自然比西式婚礼要多,具体要注意的东西,李楠只说会有人带领,我只管披上最美的凤冠霞衣就好了。
我们收拾好行李,天还没亮就起床准备出发。
路途实在太遥远,坐飞机花了四个钟,还要辗转火车,下了火车乘坐三小时的大巴车终于到了县城。
我对家乡的县城的印象比对村里的更少,我几乎没出过县城,小时候去过最远的地方还是步行两个钟到上学的镇上。
我和李楠提着行李,正在原地等着他的父母来接我们,我们在二月份的室外等着直哆嗦,大约等了半个钟,一对年老的夫妇朝我们走了过来。
那对夫妻脸上挂着笑,不知为何,我总觉得他们因岁月而下垂的苹果肌有些僵硬,看着怪渗人的。
想来应该是李楠的父母了,我不动声色观察他们,实在找不到李楠和他父母的相似之处。
长得完全不像。
03.
李楠的母亲亲昵的拉过我的手,拍了拍我的手背,笑道:“你就是萱萱吧?我家阿楠经常提起你,坐车辛苦了,现在就回家吧。”
李楠母亲手中粗粝的茧子磨得我有些疼,我甩开这些不礼貌的想法,面上也堆起笑意。
我和李楠母亲走在前面,没有李楠在身边我感到有些不安,可当我回过头看向李楠时,我感到不解。
李楠和他的爸爸正面目表情的走着,没有父子因许久未见的寒暄,也没有父亲对儿子和蔼的笑意,他们就这样静静地走着。
明明周遭人声嘈杂,我的心却静的可怕,呼吸变得急促,好像有什么东西被我忽略了。
李楠母亲突然攥紧了我的手,我浑身一僵,朝她看去,只见她对我笑了起来,浑浊的眼睛让我看不清她的情绪,只听她笑声低沉:“萱萱啊,我们以后就是一家人了。”
我点点头,压下心底的异样。
这是一栋自建别墅,路过的邻居冲着我们笑了笑,上下打量了我两眼,笑道:“老李家,这是儿媳妇呢?”
李楠爸爸木然的脸上终于浮起了几分笑意,他点头回应:“是啊,明天就过门咯。”
邻居笑着祝贺,也不知是不是我过于敏感,那投在我身上的视线变得粘腻和迫切。
终于回到了李楠的家,家里也都是一片喜庆的氛围,楼梯和墙壁都贴了囍字,客厅门口贴着对联,白色的天花板挂着红色的纸灯笼。
偌大的独栋别墅却依旧冷清,李楠看我太拘谨,等吃完了晚饭,牵起我的手带我熟悉家里的布局。
我指了指最上面,问道:“那里是做什么的?”
李楠抿了抿唇,视线却没有随着我的手指看过来,随意道:“那个是阁楼,就放些杂物,平时没事不要进去,很脏的,还有老鼠。”
一听到老鼠,我打消了参观阁楼的念头,他又笑道:反正这里以后也是你家,到时候打扫完阁楼你再进去,回房间睡觉吧,做了一天的车也累了。”
李楠带我回到房间,房间的布局很简单,只是一张两米的大床铺着大红色的床单和棉被。
已经是晚上十点,我独自一人躺在床上,李楠因婚前不能和妻子同睡为由去了别的房间休息。
陌生的环境让我难以入睡,我们老家是南方,虽冷却没有供暖,盖了两层棉被的我却依旧感到寒冷。
与北方干燥的冷风不同,是那种潮湿的阴冷。
我手脚冰冷,蜷缩在被窝里,周围安静到能够听到自己不算平缓的心跳,紧绷的神经没有因为明天的婚礼而感到缓和。
心底的异样不断蔓延,在李楠带我参观完家里之后,我总感觉有一种违和感,露出的那一点苗头却不足以让我连根拔出。
咚——
我攥紧被子,下唇被我咬得泛白,厚重的棉被无法带给我安全感。
此刻心底升起的一股毛骨悚然,随着刚刚那陡然的响声而遍布四肢百骸。
我手脚冰冷,额头却冒着汗,狂跳不止的心脏敲打着我的耳膜,最终我还是鼓起勇气掀开被子朝着声响的源头看去。
原来是墙壁挂着的灯笼掉了。
我松了口气,看了眼没关紧的窗户,许是被风吹掉的吧,我起身捡起灯笼挂了回去,并把窗户关严实。
咚——
刚关上窗户的我僵硬在原地。
04.
我努力保持镇定,早已适应黑暗的眼睛却不敢往回看,口水的吞咽声在寂静的环境中格外的响,我转过身,看向床边那个朱红色的衣柜。
声音是从里面发出的,似乎有什么东西撞到了柜门。
柜门贴着两个喜字贴,艳红的色彩在昏暗的环境中显得尤为突兀,明亮的高饱和度带有一种攻击性,心底的不安快要把我吞噬掉。
我其实可以不去管到底是什么东西掉了,可是身处陌生环境,对于未知的东西充满了恐惧,只有亲自确认才能确保安全。
我将灯打开,明亮的光充盈视线,我不再害怕,走到柜门前,伸手一拉——
一个纸扎人倒在了我的怀里。
诡异瘆人的一幕冲击着我的大脑,恐惧再次袭来,我抑制不住尖叫响彻整个房间。
明明毫无重量的纸人,压在我身上我却感到沉重无比,我颤抖着手将它推倒在地,我的余光瞥到柜子深处还有一个纸扎人。
被恐惧围困的我牙齿都在打颤,我扶着床沿,哆嗦着跑到门口,正当拉开门跑出去时,门口响起了焦急的敲门声。
‘咚咚咚——’
“萱萱?你怎么了?!”李楠直接推开了门,看到了我煞白的脸,语气担忧:“又做噩梦了吗?”
看到了李楠仿佛看到主心骨的我立马扑倒他的怀里,温热的体温让我被吓得散乱的思绪渐渐回笼,我不想再看那个不应该出现在婚房里的纸扎人,抬手指了指衣柜。
李楠却面色平静,安慰我:“那个纸人是等我们明天结婚用到的,爸妈说是习俗。”
我不理解,惊恐得看着他:“结婚为什么用纸人?”
李楠解释:“在结婚当天需要焚烧它们,意思是烧掉新郎新娘结婚前的晦气。”
这个解释似乎挺合理的,但我还是感到害怕:“可以把它们拿到别的地方吗?”
“不可以哦。”李楠将掉落的纸人塞回柜子中,并哄我上床睡觉:“乖,就一晚,忍耐一下,好吗?”
李楠用着不容置疑的语气回答我,一向迁就我的李楠此刻变得强硬起来。
我感到陌生。
李楠离开了,房间再次陷入黑暗。
对于李楠对纸人的解释,我没有完全相信,现在细想下来,有很多端倪。
虽然没来得及细看,但纸人藏在衣柜里的画面太骇人,以至于印象十分深刻。
那惨白的脸上画着两坨红晕,嘴角上扬的弧度若有似无,身上的衣服却不是纸扎的,五彩斑斓的古装衣服更显诡异。
不对劲的地方在于这对纸扎人,明明是一对男童和女童,怎能代替新郎新娘挡灾呢?
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,就开始生根发芽,从踏进来的那一刻,一切违和的地方悄然浮现。
我打开灯,明亮的环境让我起到一个镇定的作用,我盯着对面洁白的墙面,四周除了贴着喜帖,和挂着红色的纸灯笼外,再也没有任何东西。
没有任何东西。
我蓦然瞪大双眼,我终于找到了不协调的地方。
是相册。
一个家庭,一个幸福美满,没有矛盾的家庭,家里的墙面通常会挂着全家福,即便家里没有挂相框的习惯,床头柜,书桌,总会有记录家人生活状态的照片。
可我却一张照片都没看到。
是没有,还是藏起来了?藏起来是为了隐瞒什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