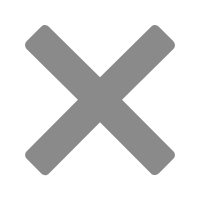-
冬日富士山
1
我是个瞎子,开了间花店。
曾有位先生经常来店里买花,他总亲切地叫我小月亮,
他说多亏我的话他才会继承警号当上警察。
后来我获得了眼角膜移植的机会。
再次睁眼,第一时间就想见他。
但无论怎么找,我都再找不到他。
【1】
岑询死在一个雪夜,隔天我才通过新闻知道他死亡的消息。
他是一名缉du警,也是我的男友。
他会和我一起种花,会给我唱最喜欢的富士山下,会耐心给我描述世界的样子,会握着我的手与我并肩走在街上,也会偷偷带价格不菲的礼物回来给我惊喜,总是不遗余力地对我好。
出任务前,他告诉我:“这次的任务很棘手,估计得多几个月才能回来了,等我这次回来给你个大惊喜!”
我莞尔一笑,对他说:“小心点,你平平安安回来对我来说就是惊喜。”
岑询语气里充满自信:“保证完成任务!”
临行前我送给他一朵栀子花,他弯腰在我唇上轻轻一点,这是我们第一次接吻。
我踮起脚尖环住他的脖子,加深了这个吻。
一吻结束,岑询爽朗一笑,说:“下次见,小月亮。”
这晚,他送我的项链吊坠断了。
我隐隐约约有不好的预感,但这条项链已经戴了四年,会断很正常,我安慰自己只是个意外,但心里还是忐忑不安。
半个月过去,岑询给我打了个电话,告诉我他那一切顺利。
岑询不会骗我,打完电话我确信吊坠断开是意外,悬着的心终于放下,我开始全心全力照看花店。
可之后岑询打电话的频率逐月下降,从离开的第六个月开始一个电话都没打过来。
我尝试主动联系他,但岑询手机关机,接收不到任何信息。
我的心情再次忐忑起来,做事也变得心不在焉。每早睁开眼的第一件事就是看看有没有岑询的信息。
九个月过去,我终于又接到岑询的电话,他在电话里告诉我,前几个月执行秘密任务不能联系外界,现在收尾,预计下个月就能结束回去了。
他的声音欢快无比,问我:“你猜猜我要给你什么惊喜?”
我想了想他常送的礼物,回答:“首饰吗?”
“对,但这次的首饰比较特殊,你收到一定会大吃一惊。”
会让我大吃一惊的首饰,难道是.......戒指?
我很配合的嗯了一声,没有把猜想说出来。
毕竟如果被发现就不算惊喜了,我不想扫岑询的幸。
岑询最后留下两个字:等我。
隔天我找到专业修首饰的老师傅把项链修好,重现佩戴起来。
回去途中路过CD店,我进去买了陈奕迅的专辑,又买了台播放机,放在花店。
岑询回来看到会有什么反应呢?我很期待。
日历上的日期慢慢都画上叉,两天后十一月五日,这天是岑询第一次来我花店的日子,也是这天,他要完成任务回来了。
两天后我没等到岑询回来,等到了缉毒警牺牲的新闻。
新闻播报员的声音如往常般舒适自然,可听到我耳中却是每一句抖刺耳难耐。
“昨日,一卧底缉毒警被毒贩发现,惨遭毒贩虐杀,死相惨重,其尸体于今日凌晨五点在废旧大楼外被队友发现,已被大雪覆盖时间长达12小时。”
脑中骤然嗡鸣响起,我劝说自己:不会的,这不一定是岑询。
新闻继续播报:“他的执法记录仪未被销毁,让我们来一起听听他临死前的声音。”
电视里传来歌声:“五...星红旗迎...风飘扬......胜利歌...声多么响亮,歌唱.....”
男人咳嗽了声,声音浑厚,像是掺着血。
他强撑着唱下去:“我们....亲爱的祖国,从今走向.....繁荣富强。”
男人的音色,分明跟给我唱富士山下的声音一模一样。
【2】
我感到全身都在不可控制地发抖,手里的盆栽摔到地上,播报员继续说:“死者手中紧攥着一枚月亮戒指,衣领里有一朵干枯的栀子花。”
我有些恍惚,分不清这是梦境还是现实,双膝一软,我“咚”地一声瘫坐在地上,花盆的碎片划伤了腿,此刻我却感受不到任何疼痛,只觉得心脏像被人紧紧揪着,难受的喘不过气。
明明岑询跟我说会回来的,他第一次骗我。
我该恨他言而无信吗?或许吧。
可我都还来不及多爱他,他就抛下我走了。
我想站起来,但腿不听我使唤,一次又一次摔下去。
眼眶很酸涩,我却流不下一滴眼泪。
岑询送我的项链吊坠这时又断了,明明前不久才刚拿去修过,维修师傅的手艺真差。
我就这么坐在地上,把头埋进两腿间,心里是前所未有的无尽失落,就像空缺了很重要的一部分。
“为何为好事泪流,谁能凭爱意要富士山私有。”
陈奕迅的歌声从播放机传出,我喉间一哽,再也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。
爸爸闻声从楼上赶下来,我总是很坚强,从小到大都没哭过几次。
爸爸把我从地上扶起坐到沙发,问我:“怎么了?哭得这么厉害,腿都流血了,很痛吧?”
我胡乱抹去眼泪,对他摇头,“不痛。”
爸爸轻拍我的头,语气温和:“傻孩子,都流血了怎么可能不痛,我给你包扎一下。”
他从抽屉里拿出打包材料,蹲下身子帮我处理伤口。
消毒水一下下刺痛我的皮肤,理智恢复了大半,我说:“爸爸,岑询死了。”
腿边擦药的动作停住,爸爸说:“你从哪里知道的?”
“新闻里讲的。”
滚烫的热泪砸在腿上,我伸手一次次抹去,却如何都止不住。
爸爸的声音带上些轻颤:“真的......?”
我缓缓点头,两手轻捂住胸口,里面如刀割般的疼痛不依不饶伤害着我,每一次呼吸像要耗尽全部力气。
爸爸贴好创口贴,坐到我身旁抱着我。
我靠在他怀里,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
他不说话,轻拍着我的背,就像岑询朋友牺牲那次,我也是这样安慰岑询的。
岑询的队友一天后来到我家,将那枚月亮形戒指交给我。
“真可惜,就差一点了。”他的声音酸涩,说完竟也呜咽小声哭起来。
“岑询每天都会提到你,他总跟我们说这次任务结束他就要向最爱的人求婚了,最后那晚他激动的一宿没睡,原本一切都很顺利的,没想到......”
我攥紧手里的戒指,尖锐的月牙嵌进肉里,渗出鲜血。
我脑中回荡起他和我说的最后一句话:“等我。”
真是个大骗子,又失约。
岑询出任务前签了器官捐献遗嘱,也许他早就想到会有意外了。
我被推上手术室,获得岑讯的眼角膜移植。
再次睁开眼,世界恢复了光明,所有事物都清晰印入我眼中,唯独没有那道令我魂牵梦萦的身影。
爸爸和岑询的队友站在床边,他们都眼眶通红,紧抿唇瓣不让眼泪落下。
一位看着约莫四十来岁的女人从门外走进,她脸上带着未擦泪痕,眉眼间是藏不住的柔情,见到我后眼中的泪水再次翻涌而出。
她快步上前走到病床边,一手轻柔抚摸着我的脸庞。
“小月,我是岑询的妈妈。”
【3】
她弯眉尽力扯起一个笑容,语气微哽:“阿询这孩子,高中时谁的话都不听,有一天突然转性开始学习了,我怎么问他都不告诉我理由。”
她吸了吸鼻涕,继续说:“直到上次走前他才肯告诉我,是因为高中有个女孩在他最颓废的时候点醒了他,他才得以迷途知返。”
“他还告诉我,现在他和那个女孩在一起了,打算任务结束就向她求婚。他平时大大咧咧活得没心没肺的,喜欢你这件事却一个人偷偷隐瞒了九年。”
女人睫毛轻颤,别过头悄悄擦了下眼泪。
“他走前跟我说,妈,如果我没回来,你就叫她忘了我重新开始吧。”
“他当时的说得轻轻松松,好像真的毫不在意。但我是他妈妈,孩子的想法我怎么会看不出来呢,他分明是想你能不要忘记他。”
女人捂着眼啜泣发抖,再说不出话。
我将手心舒展开,里面是岑询没能送给我的戒指。
岑询,你觉得我怎么能忘的掉你呢?